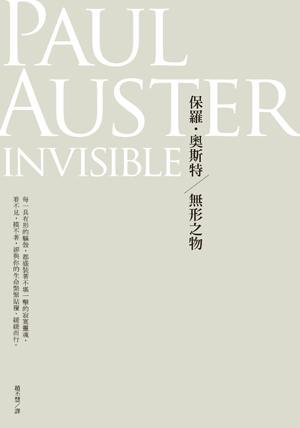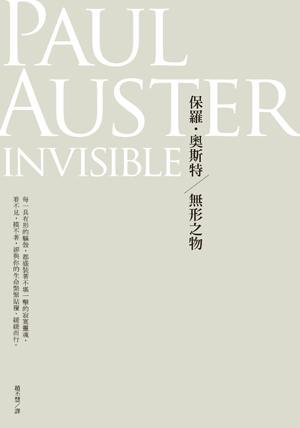內容試閱
我回家了。犯不著再等救護車,所以我回頭爬上山坡朝百老匯走往鬧區。我心中一片茫然,思緒無法連貫,等我打開公寓門鎖,我才發現我在啜泣,而且已經啜泣好幾分鐘了。幸好我的室友不在,省得我還得跟他說話,我回房間繼續哭。等眼淚收乾,我一把撕毀波恩的支票,將碎片裝入信封,第二天一大清早就郵寄給他。我沒有附上解釋。我確信明眼人一看就了解箇中含意,他會明白我跟他從此一刀兩斷,我也不想跟他那本污穢的雜誌有任何牽扯。
那天下午,《紐約時報》的晚報刊登了一則消息:十八歲的賽德瑞.威廉斯被棄屍在河濱公園,胸口和胃部有十二處刀傷。我毫不懷疑是波恩幹的。我一離開去叫救護車,他就把流血的威廉斯抬起來,扛進公園,做完他在馬路上做的事。河濱大道熙來攘往,竟然沒有人看見波恩帶著一個人過街,實在不可思議,可是根據報上的說法,調查的員警至今仍查不出蛛絲馬跡。
我是局內人,顯然有義務要打電話給當地的警察局,把威廉斯意圖打劫反遭波恩刺死的事說出來。我是到大學部學生活動中心一樓的小吃部「獅穴」喝咖啡時看見報紙的,喝完咖啡後我決定走回我在一○七街的公寓,從公寓打電話報警。我還沒有向任何人透露發生的事。我打過電話給在波啟普夕的姊姊,唯有對她我才準備吐實,可是她不在。等回到公寓,我先到大廳拿郵件,之後再等電梯上樓。我的信只有一封:沒有郵票,是寄信人親自送來的,信封上用粗黑的字體寫了我的名字,折了兩折,從窄窄的收信口塞進信箱。我搭電梯到九樓,在電梯裡拆信。什麼都別說,沃克。別忘了:我還留著刀,可不怕使用。
底下沒有簽名,不過也不需要。這是在恫嚇,可我親眼見過行動中的波恩,親眼目睹了他的殘暴,我很肯定再來一次他也不會遲疑。只要我敢出賣他,他就會追殺我。而要是我保持沉默,他就會放過我。我仍然沒放棄報警的計畫,但那天就這麼過去了,接著,更多的日子過去,我就是無法鼓起勇氣報警。畏懼逼得我緘默不語,然而事實卻是唯有緘默才能讓我不再與他有瓜葛,而我最看重的就是這一點:讓波恩從我的人生中徹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