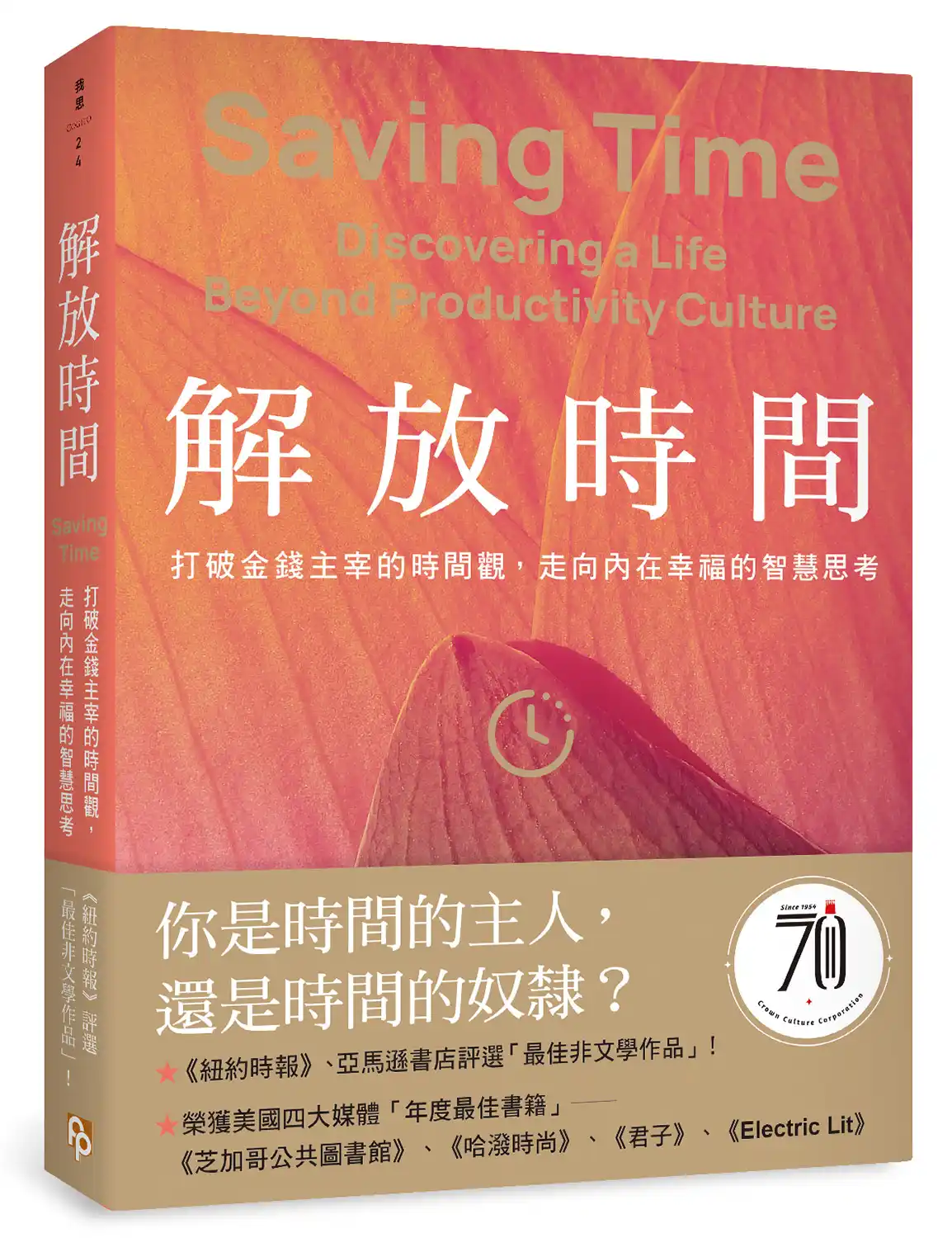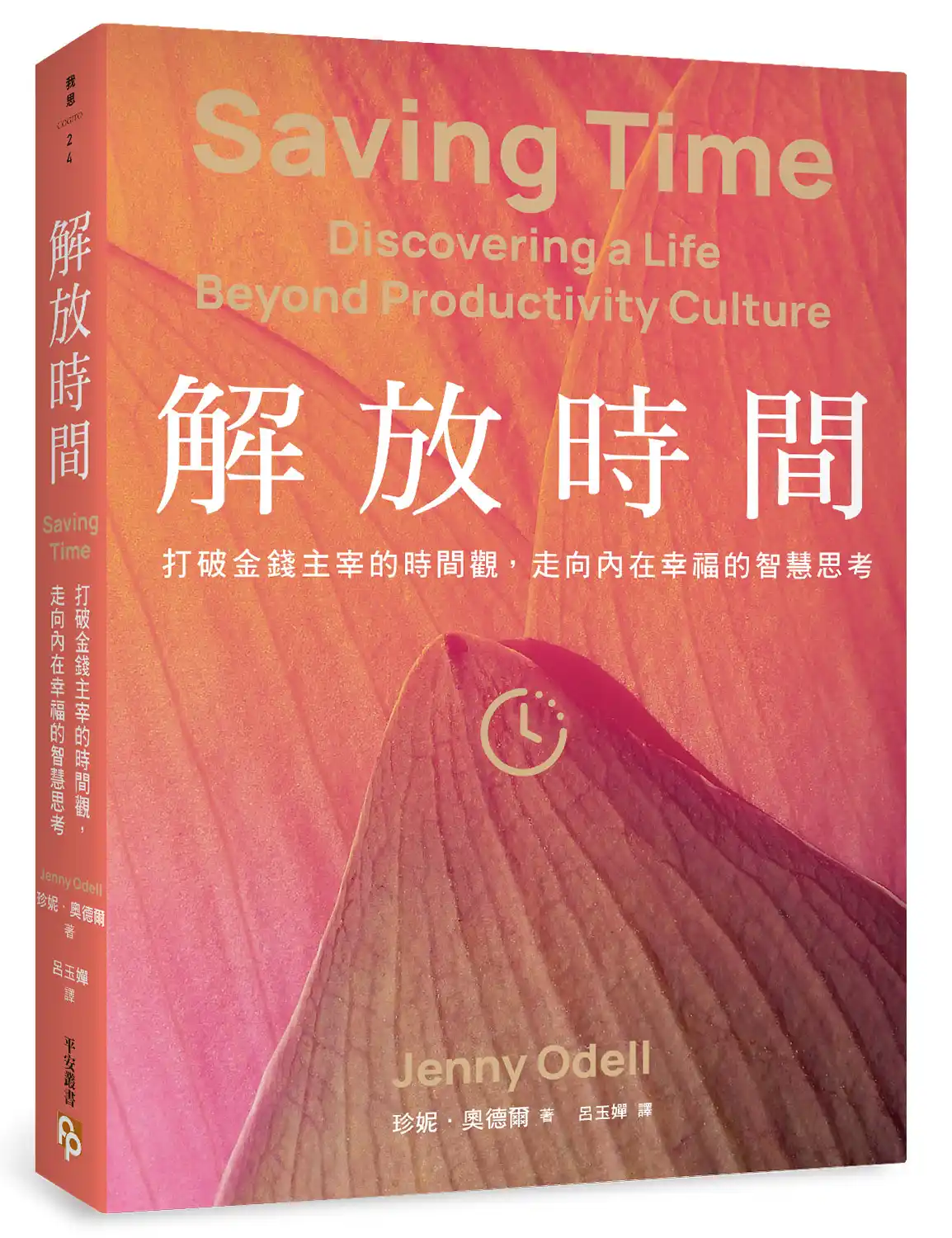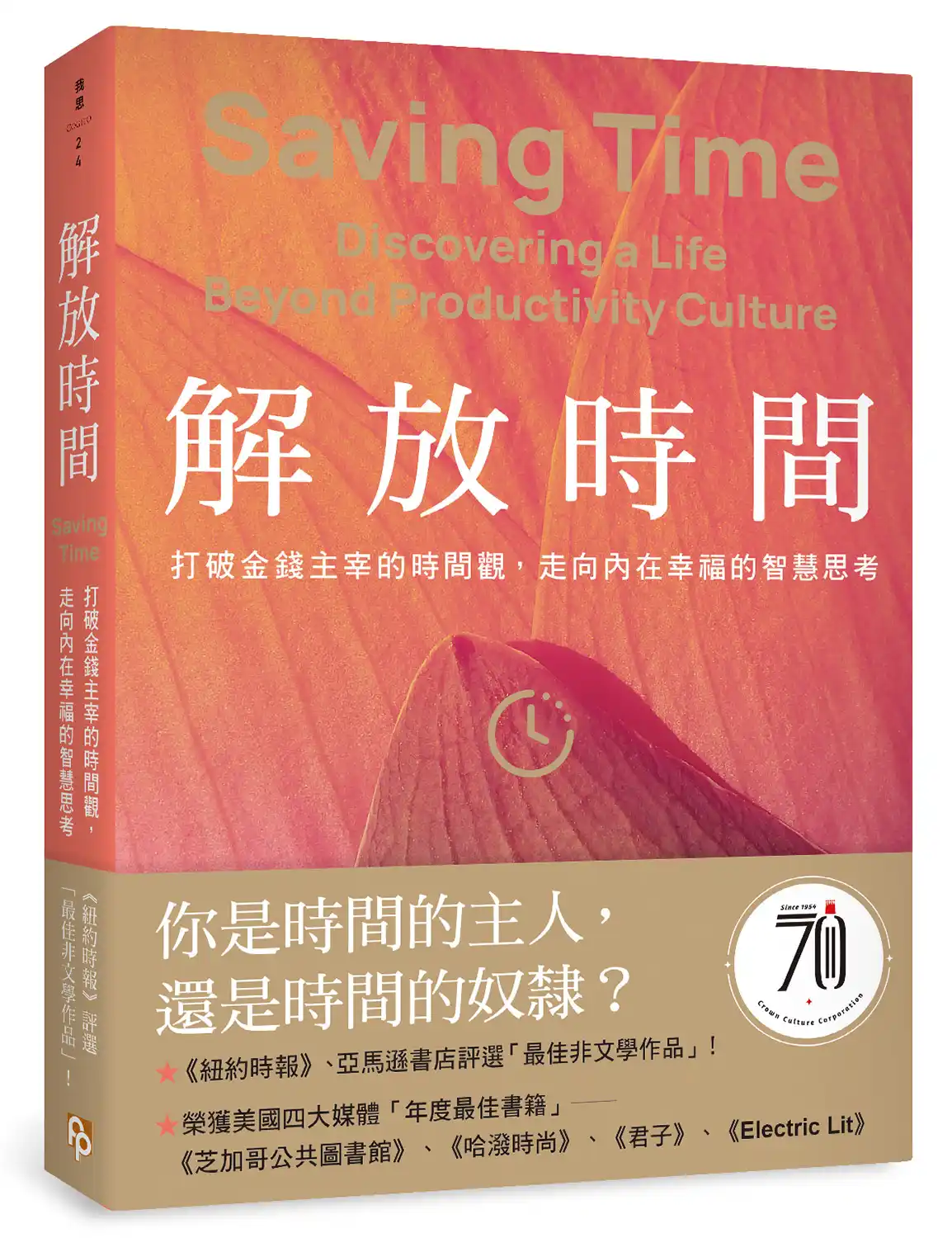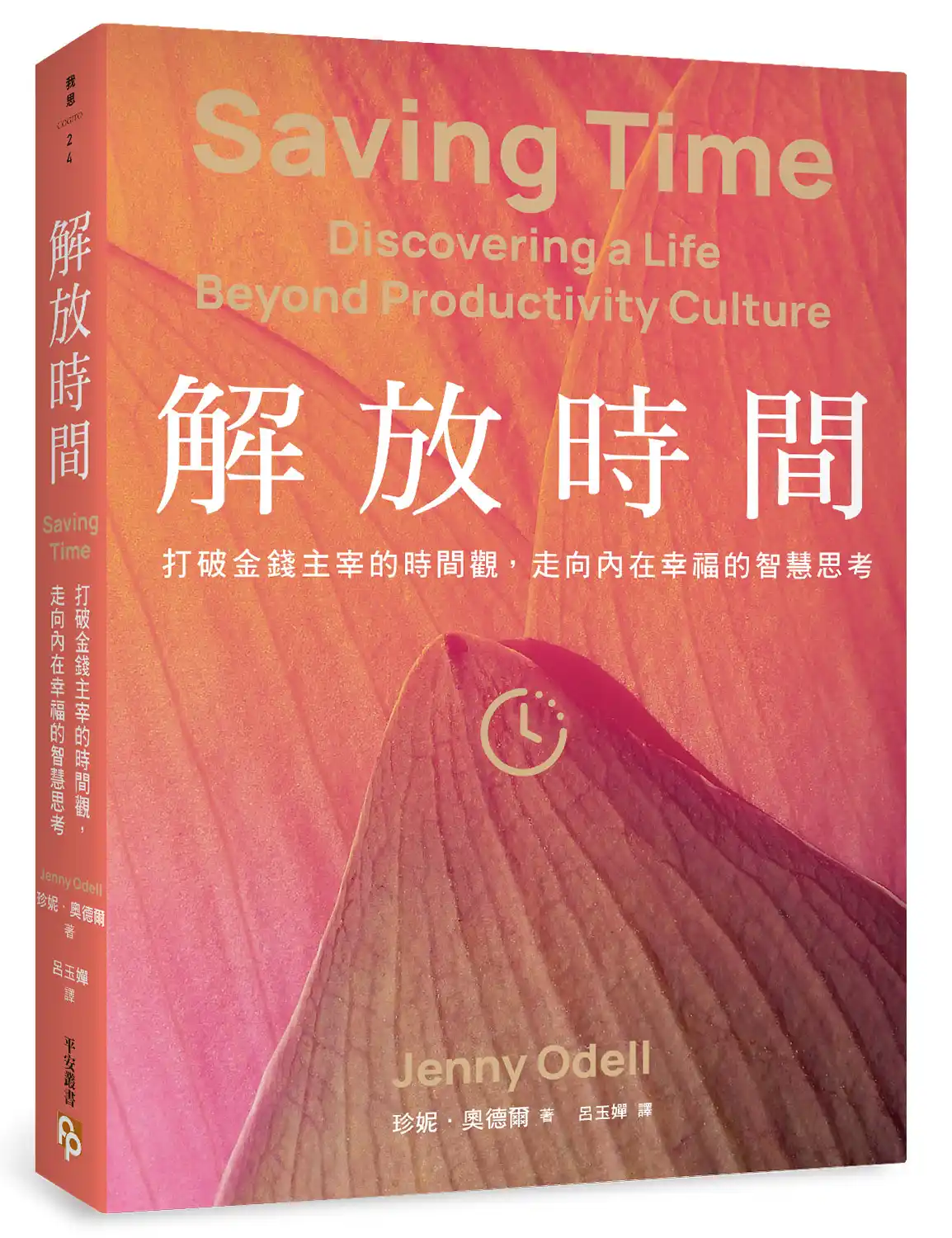內容試閱
獻給這段時間的一封信
二○一九年的某個春日,我驚覺公寓來了不速之客,它顯然沒走大門,而是直接從窗戶登堂入室。我渾然不覺好些時日,直到偶然瞥見窗邊小豬造型陶瓷花盆冒出苔蘚葉片,才知道我們被入侵了。
苔蘚孢子在一株小小的兔耳仙人掌四周安家落戶。仙人掌是幾年前友人送的生日禮物,我素來討厭廚房窗邊那塊地方,又濕又冷,從來照不到太陽,仙人掌八成也不大喜歡。不料苔蘚卻覺得那是個生長的好地方,開始分裂,形成不同的特徵,毛狀假根抓住盆中土壤,長出綠色小葉,又長出細長的孢子體,準備效法它在公寓外的祖先。一個微型森林轉眼就從豬頭長了出來。
與維管束植物相比,苔蘚與水和空氣的關係相對簡單。在《三千分之一的森林》(Gathering Moss)中,羅賓.沃爾.基默爾指出,因為需要水分以及與空氣直接接觸,苔蘚的「葉子」與人類肺泡相似,只有一個細胞厚。在無樹無木的南極洲,苔蘚對於科學家而言有著類似於樹木年輪的用處,因為苔蘚會從環境吸收化學物質,自尖端開始生長,每年夏天都能「留下紀錄」。坐在廚房中,我顯然是看不懂這株迷途苔蘚寫下的紀錄,但起碼它告訴了我一件事:我還活著。第二天:仍然活著。
在Covid-19疫情封城初期,我重讀了《三千分之一的森林》。當時時間彷彿凍結,苔蘚卻在公寓內外持續生長。疫情縮小了我的關注範圍,我像一個平庸的陰謀論者,在奧克蘭四處走動,自各種奇怪角度觀察事物。苔蘚喜好縫隙,常常出現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像是公寓外人行道裂隙之間、柏油路和人孔蓋之間、雜貨店牆壁和人行道之間、磚塊之間。我逐漸發現到一件事,苔蘚的位置和苔蘚的蹤影都像是水的簽名,舉凡是積過水的地方都能長出苔蘚,但苔蘚也會及時回應雨水,一場小雨過後,它能在幾分鐘內擴大領土,變得更加翠綠。
苔蘚讓我開始思考非常短暫的時間尺度,譬如每分每秒的濕氣變化,花盆中孢子生長的瞬間。苔蘚也讓我思索起悠長的演化時間表,因為它是最早在陸地上生長的植物之一。然而,時間光譜的兩端也提醒著我們,想精確定位一個時刻(一個十分人性的願望),那是比登天還難的事情。舉個例來說吧,在光譜的一端,我發現苔蘚孢子何時正式萌芽存在著不同的意見,是遇水膨脹到一定程度時,還是胚芽管形成,細胞壁破裂之際呢?在光譜的另一端,最初的苔蘚是幾億年前某個時刻從水生藻類演化而來,但想確定這個新發展的確切「時刻」,甚至是我窗臺這位客人的物種形成,都是荒謬可笑的。
這種模稜含糊很容易延伸到其他問題上。苔蘚是否會刻意與周圍環境分開?苔蘚孢子是否被視為具有生命?如果是冰凍的苔蘚呢?像南極洲的苔蘚在一千五百年後又復活了呢?即使不談極端的條件情況,苔蘚也讓「統一時間」(uniform time)的概念變得很複雜,因為有些苔蘚物種能夠在無水的情況下休眠長達十多年,等到適當的環境條件再復甦。二○二○年,基默爾接受《信徒》雜誌(The Believer)採訪時表示,正是這種特質讓苔蘚在Covid-19疫情期間特別值得關注。基默爾說,她的學生從苔蘚扎根和休眠的本能中獲得了靈感,認為這些植物可以指導人類如何活在歷史的這一刻。
苔蘚進入我的公寓之際,約莫正是我開始構思這本書的時候,當我完稿時,它仍然繼續成長。誠然,我的這一株不可能像南極洲象島海岸的苔蘚在同一個位置活上五千年,但在這段慢悠悠的時光,它吸收了三年的陽光,呼吸了三年的空氣,見證了我在餐桌旁度過的三年,如同來自時鐘時間之外的使者,讓我的腦海充斥著各種問題─滲透與回應、內與外、潛力與迫近。最重要的是,它始終在提醒著我們時間的存在,這裡所指的時間不是想像中獨自沖刷我們每個人的那種虛無物質,而是時啟時停、汩汩湧出、聚集於縫、堆疊成山的那種物質。是等待適合的條件,總是能開啟新事物的那一種時間。
想像你在一家書店,其中一區擺著時間管理的書籍,這類書籍幫助我們應付「時間普遍不夠用」的問題,以及關於「一個總是在加速的世界」的建議:你不是必須更有效地計算和衡量自己的零碎時間,就是得從別人那裡購買時間。在另一區,你會找到人類理解時間的文化史,以及對時間本質探討的哲學書籍。如果你分秒必爭、身心俱疲,你會選擇哪一區的書籍呢?選擇第一區似乎更有道理,因為它更直接關注日常生活和實際現實。說來諷刺,我們似乎永遠都沒有足夠的時間從事「思考時間本質」這種閒事,但是我想提醒你們,我們在第一區中尋找的若干答案就存在於第二區中,因為不去探索「時間即金錢」這個觀念的社會和物質根源,我們很可能會強化一種關於時間的語言,而這種語言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
讓我們先來想一想「生活與工作平衡」與「休閒概念」之間的不同。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休閒:文化的基礎》(Leisure, the Basis of Culture)一書中,德國天主教哲學家喬瑟夫.皮珀(Josef Pieper)提出休閒概念,他寫道,在工作中,時間是水平的,屬於一種積極行動的勞動時間模式,中間穿插短暫的休息間隙,這些間隙只是為了讓我們恢復精神,以便投入更多的工作之中。皮珀認為,這種短暫的間隙不能稱作休閒,真正的休閒存在於「垂直」的時間軸上,徹底切斷或否定日常工作時間的次元,「與工作呈直角」。如果這樣的時刻碰巧讓我們恢復工作精力,那也只是附帶的。皮珀說:「無論休閒能讓人恢復多少的工作精力,都不是為了工作而存在的;休閒的意義不在於恢復元氣、提振精神,無論是精神上的還是身體上的;休閒確實能在心理、身體和精神上帶來新的力量,但這不是重點。」出於直覺,我非常認同皮珀的區分,任何懷疑生產力不是時間意義或價值終極衡量標準的人,或許也會產生共鳴。想像一個不同的「重點」,也就是想像一種超越工作和利益世界的生活、身分和意義來源。
我認為,大多數人之所以將時間視為金錢,並不是出於所願,而是出於無奈。這種現代的時間觀離不開薪資關係,雖然「必須出售一己時間」這件事現在看來很普遍,也無可置辯,但與任何一種評估工作和生存的價值方法一樣,都具有特定的歷史背景。反過來,薪資關係也反映出同樣影響我們生活中一切賦權和削權的模式:誰買了誰的時間?誰的時間值多少錢?誰的時間安排要配合誰的時間安排?誰的時間可以隨意支配?這都不是個人問題,而是文化和歷史問題,想要釋放自己或他人的時間,這些問題都必須好好思索。
二○○四年的暢銷書《慢活》(In Praise of Slowness)提供了許多寶貴經驗,包括雇主和員工雙方都能從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中獲益,因為「研究顯示,感覺能掌控自己時間的人,更放鬆,有創造力,也更有效率」。我相信每個人都希望每天能多出一些時間,但這本書提出了一個關鍵論點:如果「慢」只是為了讓資本主義機器運轉得更快,那麼它就只會變成一種表面文章,不過是工作時間水平面上又一個短暫的間隙。這讓我想起某集的《辛普森家庭》(The Simpsons)。美枝在核電站找到工作,發現那裡的員工士氣低落,她指著一名啜泣的員工,一名斜眼倒酒的員工,還有一名正在擦槍的員工,對郭董說:「我是死亡天使,淨化的時刻到來了。」為了幫上忙,美枝斗膽建議舉辦「滑稽帽子日」,播放幾首湯姆.瓊斯的歌曲。接著我們再次看到上述的三名員工:一個啜泣(戴著墨西哥帽)、一個喝酒(戴著麋鹿帽),最後一個邊扣動扳機邊走出畫面(戴著螺旋槳帽),而背景播放著湯姆.瓊斯演唱的〈風流紳士〉(What’s New Pussycat?)。「有用耶!」郭董說(戴著維京海盜牛角帽)。
我懷疑每個人渴望的並非只是一頂滑稽的帽子,同樣我也猜測,人們會身心俱疲根本不只是因為一天時間不夠用。乍看像是想要更多時間的願望,可能只是一個簡單卻龐大的心願的一部分(渴望自主、意義和目標,即使外在環境或內在壓力迫使你完完全全活在皮珀的水平軸上)工作,為了做更多工作而休息─你仍然對垂直領域(我們的自我和生活中屬於非賣品的部分)懷抱著渴望。
即使時鐘支配我們的每一天、我們的一生,它也從未完全征服過我們的心靈。在時間表的限制下,我們每個人都體驗過許多時間的變體:因等待與渴望而延展的時間、瞬間充斥兒時記憶的當下、緩慢而篤定的孕期,或是受創的身心所需要的癒合期。身為地球上的生物,我們活在不斷縮短和延長的日子裡,活在天氣中,某些花和芳芬回來拜訪年長了一歲的自己─至少現在仍是如此。有時,時間不是金錢,而是這些事物。